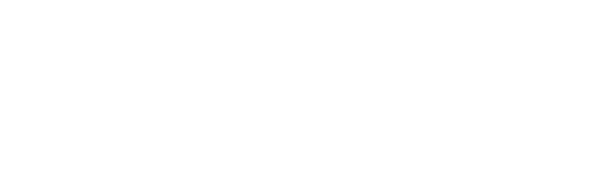摘要:虽然训练很单调,但本来家境就不富裕的海蒂并不觉得是一件多么难熬的事。即使在冬天,她也穿着一件单衣上场训练。她那时候甚至感激自己
虽然训练很单调,但本来家境就不富裕的海蒂并不觉得是一件多么难熬的事。即使在冬天,她也穿着一件单衣上场训练。她那时候甚至感激自己的教练:是他拿来一种蓝色的维生素,告诉自己这个药片可以帮助运动员抵御寒冷和伤病,是国家限定配额的重要药品。
一个小女孩因为自己的努力训练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国家的注意,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值得骄傲的事。“当时我想,每当我取得一次成功,教练就一定会发给我一粒蓝色药片。”至于这粒药片是否真的是普通维生素,她没有深究。在服用药片几周后,她的身体真的开始“茁壮成长”了:躯干肌肉群开始扩展,五官和手都迅速变大。
她的脾气比一般的逆反少年更加暴躁,变得喜怒无常。队友们也不例外,更衣室成了所有少女心事的集散地,她们中间没有人关注训练场彼端俊美的少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和队友的身上,用一天比一天低沉的嗓音谈论着日益浓密起来的体毛,然后走上训练场,投出让一般男人望尘莫及的距离。
随着姑娘们的肌肉群越来越像男人,她们需要的剂量也逐渐增加。在入学几年后,海蒂·克里格每天必须服下五到六粒“维生素”药片、接受一次“葡萄糖”注射。在教练和主管官员的目光里,她深深地感觉到了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管它呢,自己依然有子宫,依然进女厕所,还是个女人。
1986年对于海蒂·克里格来说,是值得记住的一年。在这一年的欧洲田径锦标赛上,她投出的铅球落在了21.10米的地方。她的体育生涯也停留在了这个高度。当时的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给她发来了贺电,称她为“亲爱的运动员同志”。她也许梦想着和国家领导人握手,然后几天不洗;她也许奢望着国家的舵手能够记住她的名字,哪怕只是几个月;不过,她更希望的是不吃这种善恶难辨的小药片,也可以投出20米以上的距离——但这当然是空想,21.10米对于许多男子运动员来说,也绝不是一个可以轻易企及的距离。金牌来了,名誉来了,这么多年的牺牲,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不管通过怎样的途径,海蒂·克里格的人生价值终于实现了。
这本该是一个美好的结局,是一个工人的孩子通过努力终于为国家夺取荣耀的传奇。但就像每一个童话一样,“王子和公主此后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种话,只能满足小孩子睡前的好奇。只要欢呼的人们没有健忘到冷酷的程度,便会发现冠军的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快乐。
一切都是易逝的。海蒂开始感到迷失。她经常神不守舍,像武侠小说里那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手刃仇人的侠客一样,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应该向何处去。从自己的成绩上达天听,到老大哥将她忘却,虽然前后也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但和一个残酷的青春比起来,这段闪亮的日子短得几乎微不足道。金牌在灯光下发射出耀眼的光芒,却不能掩盖青春里那段无法回忆的惨痛。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和信仰不能为自己所左右,那么他至少拥有自己的身体。就在海蒂出生后两年,席卷欧洲的“68学潮”中,就喊出了“要做爱,不要战争”的口号。在左翼知识分子的眼里,身体成为了对抗极权的武器,成为了自上而下唯一不能渗透到的地方。《1984》里的温斯顿和朱丽叶在橡树下面相会的时候,都忘记了电幕,也忘记了老大哥。
而1986年,学潮已经过去18年,当时的领导人也步入了中年。再过3年,柏林墙将倒塌,冠军的好朋友昂纳克将面临国家审判。所有的剧变都山雨欲来,但彼时的海蒂毫不知情,依然没有权力支配自己的身体。每个药瓶子的背后,都有国家权力的身影。海蒂服用的“维生素”药物产自东德最大的制药企业“耶拿药业”。
因为违背规律长期过量训练,她的身体已经到处布满了伤病,情绪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在度过了艰辛又成绩平平的4年后,1990年海蒂·克里格带着100公斤的体重选择了退役。对于一个东德运动员来说,这样的选择也就意味着实业。柏林墙刚倒下不久,西德体育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接纳东德数万名运动员和体育官员。离开了蓝色药片的海蒂·克里格一无所长。
她无法与人们正常交流,任何关于禁药的消息她都听不进去。她一直认为“那只是西德人为了贬低东德体育而造出来的谣言”。又过了5年,她才接受了这些药片的真实身份:合成类固醇,用来强化肌肉,减少疲劳感。每一粒这样的药片中,含有约30毫克男性荷尔蒙激素。“我当时丝毫没有怀疑过教练。”
海蒂说,“在东德,人们都无条件相信自己的教练,没有人想,这对我自己的身体会不会有害?”当她明白自己的身体发肤并非全受之于父母,竟有一半拜教练所赐的时候,幻灭感油然而生。从少女时代起就每天用刀片剃腿毛的她,有一天把刀片划向了自己的手腕。如今他的左手上,伤痕依然清晰可辨。离刀口不远的地方,是一枚戒指。
她变成了一个丈夫。1997年,海蒂·克里格选择了变性手术,更名为安德烈斯·克里格。他从东柏林搬到了马德堡,和妻子克劳泽生活在一起。和他一样,游泳运动员克劳泽也吃过蓝色药片。不过药效反应不太相似:在药效作用下,克劳泽的身体在几周内迅速增重,不得不过早告别了运动生涯。
这种药片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科学团队。这个项目名为STS646,领头人霍普纳官任东德奥委会委员,同时也是东德国家安全局的一员。虽然还没有任何临床数据证明这种药片可以被人类服用,但这种药片依然被分发到各项目教练的手里。当这个研究小组偶然发现一种可以使男性运动员趋女性化的药后,连霍普纳都看不下去了。他给安全局上书,要求全面停止研究,并且表明不愿为此后的任何事故负责。但在停止之前,有大约60000粒药片流向了各体工队。克里格很可能就是这批药的首批试验品。
克里格的妻子克劳泽可能吃的是另一种“维生素”。她在退役后,曾经当过护士。“我在照顾化疗病人的时候发现了一种药片,当时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教练曾经和我说,这种药是维生素。而面前这个头发几乎掉光了的癌症患者正在按照处方服用它!”
2000年7月18日,克里格和克劳泽都站在了控告兴奋剂的法庭上。据称,兴奋剂涉及到的运动员人数前后多达约10000人,其中的159人作出了和他们同样的选择。他们有的再也无法生育,有的暴饮暴食,还有人患上了肝病。运动员们曾经为之骄傲的身体,成为了后半生的拖累。这161名运动员联名控诉耶拿药业在1970-1980年之间为东德政府生产了大量合成类固醇药物,要求每人10000欧元的赔偿。主谋霍普纳对罪行供认不讳。在走下法庭前,他说:“我恳求所有受害运动员原谅我。”回答他的是沉默和一双双愤怒的眼睛。
但赔偿似乎并没有那么顺利。耶拿药业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固然和当时的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时过境迁,连国家都不复存在,一家公司如何能为历史买单?“我们都是奉命行事,类固醇也是我们企业的一项主要产品,它可以用来治疗肌肉萎缩,也可以被当成兴奋剂。是那些教练作出了错误的选择。”耶拿药业的总经理伊丽莎白·罗特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
在今天的德国,10000欧元对于一个运动员的下半生来说,简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如今离安德烈斯·克里格服用第一粒禁药已有29年,已经变身男性的他每三周就要接受一次肌肉注射,大量的雄性荷尔蒙通过这种途径进入到他的身体。说症状严重也好,说药物成瘾也好,一旦停止注射,克里格的身体就会产生强烈的反抗。“我的胡子会停止生长,同时感到六神无主。我无法使自己集中精神,经常不自主就流下泪来。我的身体告诉我,我需要激素。”
“铅球练得太多了,我的肌肉和关节都出了毛病。”当年,他曾经整个下午不喘气地做负重练习,但脊椎的永久性损伤让他甚至无法像许多他这个年龄的男人那样举起半袋面粉。“有一个圣诞夜,我爬到圣诞树下去修一个小灯泡,结果之后的整个假期,我都被迫躺在床上养伤。”
黑色的铅球上不再铭刻任何彩色的梦想。他已经不爱体育,也不爱自己的身体。对这个秃顶的中年男人来说,世界倒塌后重建的这个家庭是他的唯一。和他相比,妻子克劳泽还留存着一丝仿佛来自史前的记忆。她保存着一份证书,上面写着自己1978年在国际泳联的排名。不过从这份证书贴的位置,不难感受到这份记忆的尴尬:厕所。
安德烈斯·克里格43岁了。他在1986年得的那枚金牌,已经早就被历史的风沙融化。如今这些金子分散在每一枚“海蒂·克里格奖”的奖牌里,这是德国体育界的一个年度奖项,专门颁给与禁药作斗争的运动员和教练。海蒂被禁药杀死,却因禁药重生。
再看看这个中年男人吧。他的眼里曾经闪过女孩的娇羞,那双大手曾经抱过洋娃娃,魁梧的身体上曾经穿过带花的连衣裙。伴随一枚浮士德式的金牌,所有这些都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店里塞得满满当当的军大衣和毛毯。阳光从窗子射进这间略显老旧的商店,让灰尘的舞蹈更加夺目。一篇文章无法写完他的人生,如果光线真的像爱因斯坦说的那样可以穿越时间,让所有的光都照在他相册的第一页吧。拿里有一个尚未走失的海蒂,不知道铅球,不知道紧要,也不知道什么是来自体校的邀请。
发表于2012年8月美国《体育画报》
这是一篇德国的《举重冠军之死》。和因为举国体制牺牲的才力一样,女铅球运动员海蒂·克里格也是一位东德的国家级运动员。由于当时东德领导人迫切希望能够在体育赛场上证明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导致许多国家运动员为了成绩服用禁药。这导致了许多的运动员退役后身体畸形,甚至出现一系列人间悲剧。海蒂的故事正是他们的缩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